中国学生最缺一门课,不该被继续忽视
 音乐人赵英俊去世后,有位微博网友说,“其实我国真的应该增加死亡教育,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说再见”。
音乐人赵英俊去世后,有位微博网友说,“其实我国真的应该增加死亡教育,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说再见”。

没有什么悲伤和烦恼是会被带走的。/微博
在看不见的地方,每一分钟都有人与世长辞。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,2019年我国死亡人口998万人,死亡率为7.14‰。
换句话说,约每分钟有19人死亡,每秒钟0.3人死亡。在你读完以上句子的几秒钟里,也许已经有一个人溘然长逝。
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,这个数字大概会比常规情况有增无减,但我国的死亡教育一直滞后于欧美日韩等国家。
近日,教育部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全社会的生死教育,注重把生死教育与疫情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等紧密结合起来。

“建设课程体系,把生死教育融入课堂教育教学。”
部分院校成为第一批“吃螃蟹的人”,开设死亡教育相关课程。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,写遗书、立遗嘱、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中。
“中国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”
上世纪50年代,死亡教育相关课程与培训,宛如一阵风吹入美国各个高等院校。
一项从1975年至2005年的长期调查数据显示,在此30年中,美国有关死亡教育的讲座与短期课程,由7%发展至87%。[1]
美国独立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的院校,由1975年的7%发展到2000年的18%。开设死亡教育的院校中,学生参加培训的比例在2005年高达96%。
不仅美国大学生要接受死亡教育,更低龄的中小学生也不例外。据统计,目前美国有超6000所中小学开设生死教育课程。[2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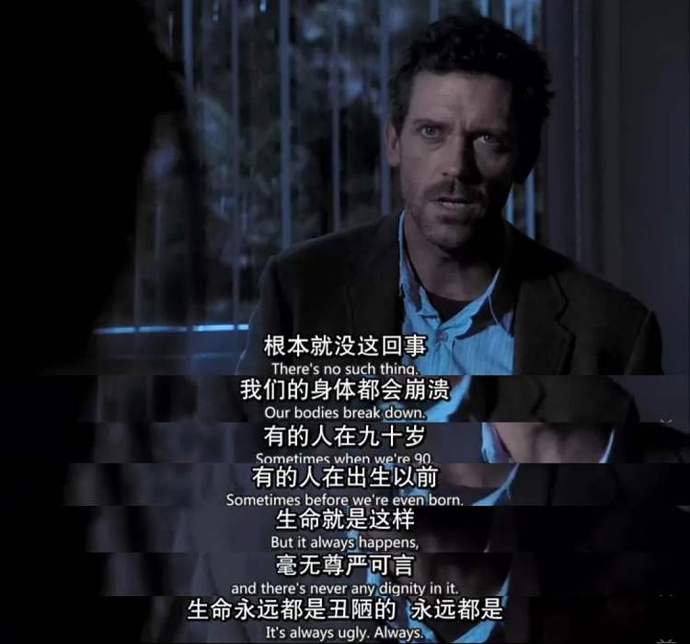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能带着尊严而活,却无法死得端庄。” /《豪斯医生》
如果得知朋友有轻生念头,你会怎么做?在加州林肯中学开展的“自杀防御课程”中,老师要求学生写一封信,假设劝说有自杀念头的朋友。
大部分美国中小学,还会聘请专业殡葬人员或重症室护士来校讲授“死亡课”。
课堂上讨论人死时会发生的状况,老师让学生模拟遇到亲人车祸死亡时的情形,或体验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。

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,谁能不悲伤呢。/《周一清晨》
美国的生死教育影响了大西洋另一岸。英国人增设死亡教育内容,并强调应将此融入思想教育或医学人文教育中,尤其强调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设计。[3]
相较于欧美国家,谈论“死”却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禁忌。
如果把目光放至文化环境与我们更为贴近的邻居——日本和韩国,会发现他们引入死亡教育的时间与我国相近,普及速度却将我们甩在身后。
在日本,东京大学成立了“生死学的展开与组织研究计划”,东京上智大学、东洋英和女学院等多所院校定期举办宣讲会,传播死亡相关知识。[4]
2004年,韩国开始推行以模拟入棺体验、假死体验等为核心的实训课程教育,并获得学员们的高度评价。[5]

模拟入棺即假装举行追悼会,体验进入棺材的感受。/《非自然死亡》
在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地区,死亡教育被纳入众多高等院校课程体系。而在中国内地,死亡教育却常年近乎缺席,已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不足20所。
是大学生不需要吗?并不。
《中国预防医学杂志》做过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,表明58.05%的大学生需要死亡教育方面的培训,仅有20.65%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可以处理现实中与死亡相关的问题。[6]
中学生对死亡教育的需求同样突出。
2020年一项针对初中生的调查指出,58.4%的人渴望在学校课堂获得死亡相关的知识,24.0%的人表示无所谓,仅有17.6%的人不渴望获得相关知识。[7]
“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,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。”主持人白岩松曾直言不讳地指出。

医学生及医护人员接触到死亡的概率,远远高于其他人。/《豪斯医生》
在美国医学院几乎全覆盖的死亡教育课程,在我国有些高校的医学院里连选修课都排不上。
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常务理事路桂军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——
在医学生的意识中,医生肩负的使命理应为救死扶伤,当面对一位医学技术已经无力回天的病人,他们会变得茫然。
求学阶段缺乏死亡教育的他们,心里很可能会有类似的疑问:
“我们的医疗体制是为生的一个医疗,所有的患者只要有一线生机,就要全力以赴,那如果一线生机都没有了,我们该做什么?其实我们并不知道。”
死亡教育,到底学些什么?
“我的墓志铭是:此处长眠着一个曾经有着美好希望的人,芒鞋斗笠千年走,万古长空一朝游,踏歌而行者,物我两忘间。”
这是广州大学一位学生在胡宜安教授开设的《生死学》课堂上为自己写下的“墓志铭”。
胡宜安被视为将死亡教育搬入中国大学课堂的第一人。
出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背景的他,发现国内的三观教育仅限于人生价值、个人价值、社会价值的讲授,而他认为生命本体是讨论价值观的前提。
为了让年轻人建立更健康的生死观,让他们对生命有透彻了解,2000年胡宜安在学校的支持下首次开设了选修课《生死学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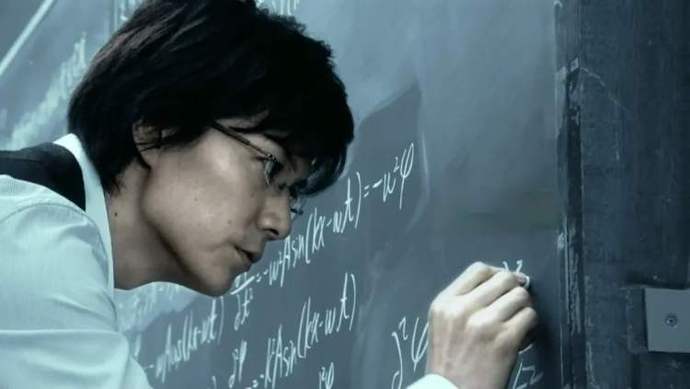
“需要有课程来科学地引导学生看待生死,避免走向极端。” /《神探伽利略》
国内没有经验可以借鉴,胡宜安便自己研究出一套教学模式,让学生们通过写遗嘱、写墓志铭的方式,来感受死亡。[8]
从最初只有三四十人增加到百余人,从小教室换到阶梯教室,《生死学》成了声名在外的网红课。
按照胡宜安的说法,这门课旨在破除死亡的神秘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。课程内容包括濒死体验、生死态度、临终关怀等。
《生死学》诞生6年后,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开设《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》,同样是热门选修课程。
据半岛网报道,一个班120个名额,需要抽签才能选到。几年前,这门课还以公开课的形式在三个高校课程平台上线,每学期都有超过2万人报名。

要抢到喜欢的选修课,可不是一件易事。/《神探伽利略》
在中国大学MOOC官网上可以看到,《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》课程大纲共分为十章,授课内容涵盖濒死体验、安宁疗护、安乐死、殡葬文化、悲伤辅导等。
线下授课时,王云岭会以学生自愿为前提,组织他们走进殡仪馆,参观告别厅、遗体存放间、遗体整容间、火化间、骨灰存放处,体验与死亡“近距离面对面”。

胡宜安、王云岭的教学尝试在国外有迹可循,写墓志铭、写遗嘱、参观殡仪馆,都出现在英美等国的死亡教育课堂上。
英国中小学开设的“死亡课”,教师们还会邀请殡葬行业或从事临终关怀的服务人员、护士等深入课堂讲授。[9]
在这些课堂上,学生们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,亲自体验丧亲等突变事件导致的情绪变化。
而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,死亡教育常常被糅合进思政教育之中,被挤到边缘一角,或在日常生活中被当作不吉利的禁忌,避而不谈。
“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同样重要”
《奇葩说》第五季,有一期的辩题是“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要不要告诉TA”。
辩手邱晨谈起自己被确诊为恶性肿瘤外加淋巴结转移时说:
“我觉得无论是死亡的日期,还是身患重病,还是我们人生中躲不过的所有的坏的消息,我们都只有看到它、面对它、甚至愿意谈论它的时候,我们才有可能去对抗它。”

马东结辩时称:“面对生死这件事,是我们所有汉文化里面的人缺的一课。”
随着呼吁重视死亡教育的声音增加,越多越多人愿意正视并谈论死亡。
2019年,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建议,从中小学生开始开展死亡教育,让人们尊重死亡、尊重生命。
他看到很多癌症晚期患者饱受病痛折磨,但家属往往会拒绝接受舒缓治疗,怕被认为是不孝。
“社会上年轻人自杀现象时有发生,我们对尊重生命的相关教育有一定欠缺。”他认为。
一些人将改变付诸实际行动,他们的尝试通过互联网被看见。
2017年,成都一所中学在体育馆开展“死亡体验”课程。老师先通过一组图片让学生感受生命的美好顽强,然后让54名初一学生蒙住双眼,躺在地板上体验“死亡”滋味。
长达20分钟的“死亡体验”结束后,学生们为自己写下“墓志铭”。有人忏悔“上课不认真,也不怎么听父母的话”,有人写下对父母的愧疚。

整个课程的设置长达1个半小时,“死亡体验”仅仅是其中一项。/图虫创意
据该校专职心理教师易姜琳介绍,课程以“向死而生”为主体,通过对生命的阐释,让学生从中领悟到生命的真谛。
去年底,常州一幼儿园开设死亡课程。在老师的带领下,孩子们若有其事地给皮球虫办一场“葬礼”。话题由皮球虫的死亡延伸到生命教育绘本。
此事登上微博热搜,在央广网发起的一项投票中,支持幼儿园开设死亡课程的有270人,占投票人数的58.6%。
有90人表示“不支持,对幼儿园孩子来说太沉重”,占19.5%;有98人认为要看具体内容、选择恰当的方式,占21.3%。
“小孩子心理素质还没那么强大,很容易会产生扭曲心理。”虽然评论区不乏类似的质疑,但总体而言,投票支持者占大多数。

在小朋友的世界里,死亡是一件遥远的事。/《再见我们的幼儿园》
同样在去年年底,一名95后女孩当寿衣模特冲上微博热搜,相关话题被43.1万人阅读。这位勇于打破传统目光的女孩,获得大部分网友的支持。
但在现实生活中,她不时遭受着误解。
在一次同学聚会中,她刚自我介绍完,旁边一个女同学很害怕,不敢转脸面对她。
因为忌讳,妈妈劝她辞职,她却说,总要有人站出来,为人们和世界的告别做一点事情。

“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成瘟神。” /微博
那些对她的职业避而远之的人,或许缺一堂教他们如何正视死亡的课。
有人将死亡教育和性教育视为一对“难兄难弟”。对此,美国作家早崎绘里香在《生死功课》里写道:
“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同样重要,甚至死亡教育比性教育更加重要。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性,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死亡。”
参考资料:
[1] Dickinson GE.Teaching end -of -life issues in US medical schools: 1975 to 2005[J].Am J Hosp Palliat Care,2006,23( 3) : 197-204.DOI: 10.1177 /1049909106289066.
[2] Doka KJ.Hannelore wass: Death education-an enduring legacy[J].Death Stud,2015,39( 9) : 545-548.DOI: 10.1080 /07481187.2015.1079452.
[3] Dickinson GE, Paul ES.End-of-life issues in UK medical schools[J]. Am J Hosp Palliat Care,2015, 32 ( 6 ) :634-640.DOI: 10.1177 /1049909114530492.
[4] Kawagoe H, Kawagoe K.Death education in home hospice care in Japan[J].J Palliat Care, 2000, 16( 3) : 37-45.
[5] Sofka CJ.Hannelore wass: The lasting impact of a death educator, scholar, mentor, and friend[J]. Death Stud,2015,39( 9) : 558-562.DOI: 10.1080 /07481187.2015.1064293
[6]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20年11月第21卷第11期,《大学生死亡教育需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》
[7] 李靖.初中生物教学中死亡教育的探析与实践研究[D].导师:吕秀华.内蒙古师范大学,2020.
[8] 《师者|广州大学教授传授生死学18载:认知死亡才能敬畏生命》澎湃新闻
[9] 周瑶瑶,黄泽政,苗波.国外与港台高等学校生命教育发展及其重要启示[J].沈阳农业大学学报( 社会科学版)
[10]《河南95后女孩做寿衣模特:帮人们在生命最后一刻体面告别》正观新闻
[11] 美国的死亡教育-《文苑》2019年第03期
[12] 美国学校的死亡教育-《校长》杂志2010年第10期
[13] 《清明节特别策划:高校生死教育——孤岛中的坚守》触电新闻
原文转自:网易新闻https://c.m.163.com/news/a/G25K7141051285EO.html?spss=wap_refluxdl_2018&referFrom=&spssid=dc7b148c24a3242d90f98da5b78cdd7d&spsw=2&isFromH5Share=article
